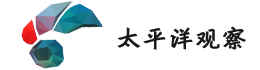
顾文豪
1960年,奈保尔获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当局提供的奖学金,前去加勒比和旧时的西班牙大陆上的前跟班殖民地举办为期三个月的游历。这时的奈保尔正陷入写作的瓶颈,依赖家园影象创作的《米格尔街》,确实为他找到了本身的文学声音,但童年素材不久即耗损殆尽,奈保尔写作的想象力“就像一块涂满了粉笔字的黑板,在各个阶段被擦干净,最后再一次成为空缺”,乃至这种写作方法此时也更多地成为一种束缚,它将奈保尔推回到一个过分窄小的天下,使他成为一个过分简朴的人。因此,这趟加勒比之旅不只为奈保尔提供了一次小憩的机遇,更成为他人生中的一段迷人插曲—作为这次观光的成就,游记《重访加勒比》为他开启了一段新的写作过程。
凭证奈保尔对付写作的界说,写作意指“一种寓目和感觉的方法”,而“每一种写作,着实都是某种特定汗青和文化的洞察力的产物”。因此,奈保尔的文学写作始终泛起出一种深入特定汗青和文化的意图—重要的不只是写什么,而是看到什么,是怎样整理、表明这个天下。在这种写作见识的影响下,奈保尔的游记从不存眷风光胜景,也有时抒发呢喃私交,岂论是他初始拜访的加勒比地域,照旧三度游历的印度,抑或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伊斯兰四国,他更愿誊写的是一个地域的文明履迹,更存眷的是这些处所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的处境,更在意的是这些国度和地域何故身处一个急速厘革的期间却一事无成?
沉着的奈保尔从未试图给出谜底。更多时辰,他是一个了如指掌的调查者和不动声色的提问人。在《重访加勒比》开篇整整40页的篇幅里,他先是记录下了在凌驾大洋的远程客轮中的游客众生相:船上的人们“按肤色划圈子,按种族划圈子,按区域划圈子,按钱多钱少划圈子”,但又没有什么圈子是牢靠稳固的,“一小我私人可以属于全部圈子”;半途上船的移民使得汽船越来越挤,头等舱的酒吧成了独一的遁迹所,这时船上只有两个阶级,游客和移民;移民首领举止得体,得体到喝茶典礼里的每个微小步调他都不会漏掉,“跟随者透过窗户赞赏地望着他”,饮茶完毕,“他当即用餐巾纸优雅地贴一下嘴唇,回到他的跟随者中,边笔底生花边雄辩滚滚,边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直到头等舱和经济舱之间的隔栏阻断了他的步履。
信手白描,琐细一般,奈保尔记录的航程旅次,在游记、漫笔与小说之间自如切换,渐渐悠悠地就将他对付移民群体的敏锐调查、西印度群岛的汗青糊涂账以及各规划盘的差异人等通盘托出,像是航船切开水面时出现的波纹,让本来安静的河水浮漾出并不常见的面孔。
虽然,奈保尔不会止步于刻画同船渡客,正如诺奖委员对他的评价,“其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论述与不为世俗阁下的试探融为一体,是驱使我们从扭曲的汗青中探寻真实的动力”,换句话说,奈保尔最大的创作特质,即在于他老是试图“从扭曲的汗青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可扭曲的又何止是汗青?奈保尔苏醒地熟悉到,身处文明边沿的殖民地人,不行停止地会遭遇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清贫,“处所狭窄,经济简朴,养育出来的人头脑狭窄,运气简朴”,更重要的是,恒久的殖民抑制,导致一种智识上的缺陷,而这种缺陷反过来却成为殖民地人自我奴役的最佳养料。
在加勒比这个一矢之地,人们既没有民族情绪,也没有反帝情感,反而是大英帝国的殖民性成绩了人们的身份认同;社会认可权利,但谁也没有尊严,服从和品格是无人欣赏的玩意;人们喜谈“文化”,但这里的文化却和一般糊口截然分隔,更像是“夜总会演出的一个节目”;阶层分界愈加固化,大家都被扣留在“由相似的幻想、相似的意见意义和利欲熏心铸成的彼此孤独的监狱之中”; 逐步吞吞、愁云满面,外貌上百依百顺,现实上独立不羁,个个都为本身糊口的一小角而莫名孤高。
在奈保尔看来,加勒比地域的人是“仿照者”,糊口在借来的文化中,他们巧于仿照,过着借来的糊口。不只在经济上,乃至在文化上、制度上、精力上以致生理上,殖民地人都全方位地陷入仿照的恶性轮回,他们没有自信念和自尊心去成立属于本身的文化和糊口,却妄图穿戴借来的衣服而成为真正的自我。于是,不行停止地,殖民地人无时无刻不糊口在一个破碎的双重天下中—一边是遥不行及的宗主国天下,一边却是对真实天下的自我意淫式的粗拙仿照。
真其实别处,真实只存在于主子的天下。民族独立,并没能将殖民地人从自卑和空虚中解放出来,“我们冒充本身是真的,冒充在进修,冒充在为糊口做筹备”。而当一个农夫思想、款子思想的社群置身于物质主义的殖民社会中,“因割断根本而在精力上裹足不前”也就不是什么料想之外的事了。
(责任编辑:张振江 HN061)
上一篇:杨福军:让老黎民糊口越来越好